二义士舍生藏孤 韩献子全节救赵
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屠岸贾与相国赵盾素有夙仇,岸贾伺机加害赵氏,无隙可趁,时晋景公以齐、郑俱服,颇有矜慢之心,宠用屠岸贾。一日梁山无故之崩,屠岸贾以“刑罚不中”,妄奏这是赵盾曾在桃园弑君而引起的。晋景公遂惑其言,问于韩厥,对曰:“桃园之事,与赵盾何与?况赵氏自成季以来,世有大勋于晋。主公奈何听细人之言,而疑功臣之后乎?”景公意未释然,复问于栾书、郤锜。二人先受岸贾之嘱,含糊其词,不肯替赵氏分辩。景公遂信岸贾之言,以为实然。秘命岸贾曰:“汝好处分,勿惊国人!”
韩厥知岸贾之谋,夜往下宫报知赵朔(赵盾之子,景公亲妹丈),使预先逃遁。朔曰:“吾父抗先君之诛,遂受恶名。今岸贾奉有君命,必欲见杀,朔何敢避?但吾妻见有身孕,己有临月,倘生女不必说了,天幸生男,尚可延赵氏之祀。此一点骨血,望将军委曲保全,朔虽死犹生矣。”韩厥泣曰:“厥受知于宣孟,以有今日,恩同父子。今日自愧力薄,不能断贼之首,所命之事,敢不力任?但贼臣蓄愤已久,一时发难,玉石俱焚,厥有力亦无用处。及今未发,何不将公主潜遂公宫,脱此大难?后日公子长大,庶有报仇之日也。”朔曰:“谨受教!”二人洒泪而别。赵朔么与庄姬约:“生女当名曰‘文’,若生男当名曰‘武’,文人无用,武可报仇。”独与门客程婴言之。庄姬从后门上温车,程婴护送,径入宫中,投其母成夫人处。
二日,岸贾奉命讨朔,将赵氏尽行诛戮,岸贾为斩草除根,派人严密监视庄姬,庄姬果生一男,谎称生女,岸贾搜索时,将孤儿藏在裤中,才躲过一劫,传言孤儿已送宫外。岸贾遂悬赏于门,“有人首告孤儿真信与之千金,知情不报全家处斩”又分咐宫门上出入盘诘。
时赵盾有两个心腹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程婴谓杵臼曰:“赵氏孤在宫中,索之不得,此天幸也!但可瞒过一时耳。后日事泄,屠贼又将搜索。必须用计偷出宫门,藏于远地,方保无虑。”杵臼沉吟半日,问婴曰:“立孤与死难,二者孰难?”婴曰:“死易耳,立孤难也。”杵臼曰:“子任其难,我任其易,何如?”婴曰:“计将安出?”杵臼曰:“诚得他人婴儿诈称赵孤,吾抱往首阳山中,汝当出首,说孤儿藏处。屠贼得伪孤,则真孤可免矣。”程婴曰:“婴儿易得也。必须窃得真孤出宫,方可保全。”杵臼曰:“诸将中惟韩厥受赵氏恩最深,可以窃孤之事托之。”程婴曰:“吾新生一儿,与孤儿诞期相近,可以代之。然子既有藏孤之罪,必当并诛,子先我而死。我心何忍?”因泣下不止。杵臼怒曰:“此大事,亦美事,何以泣为?”婴乃收泪而去。夜半,抱其子付于杵臼之手。即往见韩厥,先以“武”字示之,然后言及杵臼之谋。韩厥曰:“姬氏方有疾,命我求医。汝若哄得贼亲往首阳山,吾自有出孤之计。”
于是程婴带着岸屠在首阳山深处捉拿公孙杵臼和赵氏孤儿,闻有啼哭之声,甲士上前,杵臼一见,即欲守之,被缚不得,乃大骂曰:“小人哉,程婴也!昔下宫之难,我约汝同死,汝说:‘公主有孕,若死,谁作保孤之人?’今公主将孤儿付我二人,匿于此山,汝与我同谋做事,却又贪了千金之赏,私行出首。我死不足惜,何以报赵宣孟之恩乎?”千小人,万小人,骂一个不住。程婴羞惭满面,谓岸贾曰:“何不杀之?”岸贾喝令:“将公孙杵臼斩首!”自取孤儿掷之于地,一声蹄哭,化为肉饼,哀哉!髯翁有诗云:
一线宫中赵氏危,宁将血嗣代孤儿。
屠奸纵有弥天网,谁料公孙己售欺?
屠岸贾起身往首阳山擒捉孤儿,韩厥却教心腹门客假作草泽医人,入宫看病,将程婴秘传“武”字,粘于药囊之上。庄姬看见,已会其意。讲几句胎前产后的套语,庄姬见左右宫人俱是心腹,即以孤儿裹置药囊之中。那孩子啼哭起来,庄姬手抚药囊祝曰:“赵武,赵武!我一门百口冤仇,在你一点血泡身上,出宫之时,切莫啼哭!”分付已毕,孤儿啼声顿止,走出宫门。分咐宫人将孤儿抱出宫门,亦无人盘问。韩厥得了孤儿,如获珍宝,藏于深室,使乳妇育之,虽家人亦无知其事者。
程婴往见韩厥,厥将乳妇及孤儿交付程婴,婴抚为己子,携之潜入盂山藏匿。后人因名其山曰“藏山”,以藏孤得名也。
(前583)晋景公十七年,景公生病,占卜认为是大业的后代不顺心作崇,景公卒,悼公(前572)即位,悼公素闻韩厥之贤,拜为中军元帅,以代栾书之位。韩厥托言谢恩,韩厥就称赵氏对晋国的贡献,说出了赵氏的家世,私奏于悼公曰:“臣等皆赖先世之功,得侍君左右。然先世之功,无有大于赵氏者。衰佐文公,盾佐襄公,俱能输忠竭悃,取威定伯。不幸灵公失政,宠信奸臣屠岸贾,谋杀赵盾,出奔仅免。灵公遭兵变,被弑于桃园。景公嗣立,复宠屠岸贾。岸贾欺赵盾已死,假称赵氏弑逆,追治其罪,灭绝赵宗,臣民愤怨,至今不平。天幸赵氏有遗孤赵武尚在,主公今日赏功罚罪,大修晋政,既已正夷羊五等之罚,岂可不追录赵氏之功乎?”悼公曰:“此事寡人亦闻先人言之,今赵氏何在?”韩厥对曰:“当时岸贾索赵氏孤儿甚急,赵之门客曰公孙杵臼、程婴,杵臼假抱遗孤,甘就诛戮,以脱赵武;程婴将武藏匿于盂山,今十五年矣。”悼公曰:“卿可为寡人召之。”韩厥奏曰:“岸贾尚在朝中,主公必须秘密其事。”悼公曰:“寡人知之矣。”韩厥辞出宫门,亲自驾车,往迎赵武于盂山。程婴为御,当初从故绛城而出,今日从新绛城而入,城郭俱非,感伤不己。韩厥引赵武入内宫,朝见悼公。悼公匿于宫中,诈称有疾。明日,韩厥率百官入宫门问安,屠岸贾亦在。悼公曰:“卿等知寡人之疾乎?只为为功劳簿上有一件事不明,以此心中不快耳!”诸大夫叩首问曰:“不知功劳簿上,那一件不明?”悼公曰:“赵衰、赵盾两世立功于国家,安忍绝其宗祀?”众人齐声应曰:“赵氏灭族,已在十五年前,今主公虽追念其功,无人可立。?”悼公即呼赵武出来,遍拜诸将。诸将曰:“此为小郎君何人!”韩厥曰:“此所谓孤儿赵武也。向所诛赵孤,乃门客程婴之子耳。”于是赵武便继承原有的封邑,为答韩厥之恩,更名为“赵武子”,“赵氏孤儿案”流传古今。
太史公于《赵世家》一文中结论:“……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带始事晋,夙初在土。岸贾矫诛,韩厥立武。……”
《韩世家》一文中结论,太史公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
根据《史记》选自《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六回、第五十七回(题目编者所加)
淮南《平氏族谱》编纂委员会
战国七雄之一 —— 韩国
韩国是周朝的诸侯国,为战国七雄之一,史学家将韩、魏、赵、秦、楚、燕与齐合称战国七雄。韩国国土主要包括今山西南部及河南北部,初都阳翟(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灭郑国后迁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建立,建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县)。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迁都新郑(今河南郑州)。前325年魏惠王与韩宣惠王(韩威侯)在巫沙会面,并尊为王,所在地设置颍川郡。
韩国以其著名的兵器--弩,为各国所畏惧。所谓"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国的弩能射八百米之外,"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除此以外,韩国的剑也异常锋利,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
韩国国势最强是韩昭侯在位时。他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政修明,韩国成小康之治。由于地处中原,韩国被魏国、齐国、楚国和秦国包围, 所以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国土也是七国之中最小的一个。
曲沃桓叔庶子韩万,因协助曲沃武公由曲沃克晋,被武公封于韩地,繁衍氏族,在韩献子在位时成为晋的门阀名卿,传至韩康子。
前455年~前453年,韩康子与魏桓子奉智伯之命,在晋阳之战中,讨伐赵襄子。最后韩、魏倒戈,与赵合灭智伯,瓜分了智伯所有食邑。从此韩、赵、魏三卿世族独霸晋政。三卿再将晋的领地瓜分,是为三家分晋。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晋三卿为诸侯,韩国正式立国。国君为姬姓韩氏,是晋国大夫韩武子(晋武公叔父)的后代。
由于地处黄河中游地区,韩国东部和北部都被魏国包围、西有秦国、南有楚国、以及有当时已很薄弱的东周(洛阳),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在昭侯时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迅速衰落。屡遭列强欺凌。早年已经为魏齐之间的争霸资本,于前341年的马陵之战是围魏救韩的结果。秦楚争霸时,秦又要挟韩魏共同伐楚。战国末期,韩国成了秦国和齐国之间战争的缓冲地,苟延残存;前265年,秦国大举进攻韩上党,上党不愿被秦占有,改降于赵,引发了长平之战。两场决定霸主局势之战都由韩国而起,充分体现了韩国被列强围欺鱼肉的困境。最终于在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
公元前1040年武王灭商后,周朝实行分封制,大封诸侯。周成王时,周公旦摄政,平息了商纣王子武庚和管叔、蔡叔的叛乱。成王再次分封,封其弟于唐,号唐叔虞。国在燕国之西,即今山西河津县东北。因在晋水,后改成晋,韩国的先人春秋时为晋国大夫,受封于韩原(今陕西韩城)。春秋末年,韩贞子迁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至公元前230年韩国灭亡,历时173年。韩国先后13位君主,其中后五任称王,王国历时一百零四年。史载,韩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迁入晋国后被封于韩原《史记·韩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八里。又在韩城县南十八里,故古韩国也。"《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采于韩原故城也。"今陕西韩城县境内。,遂以封地为姓,始有韩氏。由韩氏部族而诸侯,而战国,漫长几近千年的韩人部族历史,有两个枢纽期:
第一个枢纽期,春秋晋景公之世,韩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韩厥时期。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其时,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剪灭赵氏的重大事变。在这一重大事变中,韩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赵盾无罪,后又保护了"赵氏孤儿"赵武,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赵武重新得封,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起用京人(京,战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申不害进行了变法。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军备。使韩国国力大增,十数年间,诸侯无侵者。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韩哀侯(韩屯蒙),战国时期韩国国君。前376~前374位,开国君主是春秋时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武子的曾孙韩厥以封邑为氏,称韩氏。韩起又称韩宣子,是韩厥之子,宣子徙居州。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宣子与赵简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韩贞子代立。贞子卒,子韩简子代;简子卒,其子韩庄子代;韩庄子卒,其子韩康子。韩武子:韩康子的儿子。武子二年,伐郑,杀其君幽公。十六年(前496年),武子卒。韩景侯(?—前400)战国时韩国国君。名虔。晋卿韩武子之子。
哀侯元年(前376年)韩、魏、赵共废晋靖公而分其地,晋国灭亡。次年韩灭郑,迁都于郑都新郑(今河南新郑),疆域包括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 《资治通鉴》记载哀侯以韩廆为相而爱严遂,二人水火不容,前374年严遂指使杀手在朝中刺杀韩廆,韩廆走到哀侯处,哀侯抱之,结果杀手刺中韩廆时也连带杀了哀侯。《史记·韩世家》则称“韩严弑其君哀侯”。哀侯之子懿侯(或作庄侯)继位,将国都迁回阳翟。继任:子韩懿侯。哀侯少子婼食采平邑而以邑为氏,少子婼是平氏的得姓始祖。
政治政策
韩哀侯时期,韩国政治混乱,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韩哀侯实行改革。继续推行申不害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
国君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符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并根据考察的结果进行赏罚,提拔重用忠诚可靠之臣,贬除狡诈奸滑之人。最好采取隐密的权术,表面上不露声色,装作不听、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国君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从而“独断”。
韩哀侯时期,申不害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史称“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需要指出的是,申不害的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效果远不如魏、秦等国。
韩哀侯时期的韩国在现在的河南一带,《史记》上有这样的记载:“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於韩原,曰韩武子。”也就是说,韩国祖先最初是被封于“韩原”这个地方的。致韩厥之时,列为晋国六卿之一,即“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
献子之子宣子徙居州。宣子子贞子徙居平阳。至于“郑”这个地方,最初不是韩的领土,而是另外一个诸侯国——郑国。《史记》记载“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我们知道,春秋与战国分野的标志就是韩、魏、赵的三家分晋。所以,说战国时期的韩国都城应该是郑。《史记》记载韩哀侯时期韩的疆域范围,韩的领土范围大致应是黄河以南,故不包括河北,在颖水之滨,故在河南界内,郑州、洛阳之间,西北与山西接壤,南不过淮河一线(当时是楚地)。
韩哀侯时期的韩国,铁制农具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耕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建国后考古发现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铁铧、镢、锄、镰等。铁农具的推广和使用,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和耕作效率的提高。
韩哀侯时期牛耕在战国时期更加普遍。铁农具和蓄力的结合,为深耕细作提供了条件。《韩非子外储说上》说:“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如果没有畜力和铁农具,深耕细作是不可能的。
农民在长期的耕作实践中,生产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已经能从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程度去认识和区别土壤,因地制宜地进行耕作,农民已很重视对土地的施肥,“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韩哀侯时期,通过施肥改良土壤,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随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有的地方还推广了一岁两熟制,《荀子富国》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总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十分迅速,生产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经济措施
韩哀侯时期,手工业发展迅速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小农经济成为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男耕女织,其产品主要是满足家庭的需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个体手工业。指民间具有一定专门技能的工匠,依靠自己的“技艺”从事的小商品生产,他们分布于各个行业中,如木工、皮革工、鞋工、陶工、漆工等,其产品多是自产自销。私营手工业。指“豪民”经营的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如猗顿经营的煮盐业,卓氏和孔氏经营的冶铁业等,其劳动者主要是依附农民、雇工和奴隶,私营手工业要向国家交纳赋税,个别大手工业主积累了大量财富,富比王室。官营手工业。一般规模较大,由官府设立专门官吏掌管,生产者由奴隶,罪犯和雇工,其产品主要是兵器、礼器及生活奢侈品,主要用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
韩哀侯时期,韩国商业也很发达,主要表现在商人的活跃,城市的繁荣和货币的流通等方面。
韩国商人们贩运于列国之间,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各地的特产如北方的马匹,南方的鱼,东方的盐,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场上都能买到。大商人更加活跃,如大商人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史记货殖列传》)大搞投机交易,赚取了大量财富,河东盐商猗顿和冶铁商郭纵,富甲天下交结诸侯,干预政治,阳翟大贾吕不韦,通过贩贱卖贵,家至千金,参与政治,官至丞相。
韩哀侯时期,城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韩之阳翟(今河南禹县)。
韩哀侯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金属货币的流通更加广泛了。当时金属货币有铜币和金币两大类,铜币主要有四种:燕、齐两国使用刀币,周、秦一带使用圆钱,三晋使用布币,楚国使用“蚁鼻钱”,金币一般以斤(十六两),镒(二十两)为计量单位,还有“饼金”和“郢爰”。(饼金为饼状金块,郢爰为方形金块)金属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中华平氏总谱》执行编委会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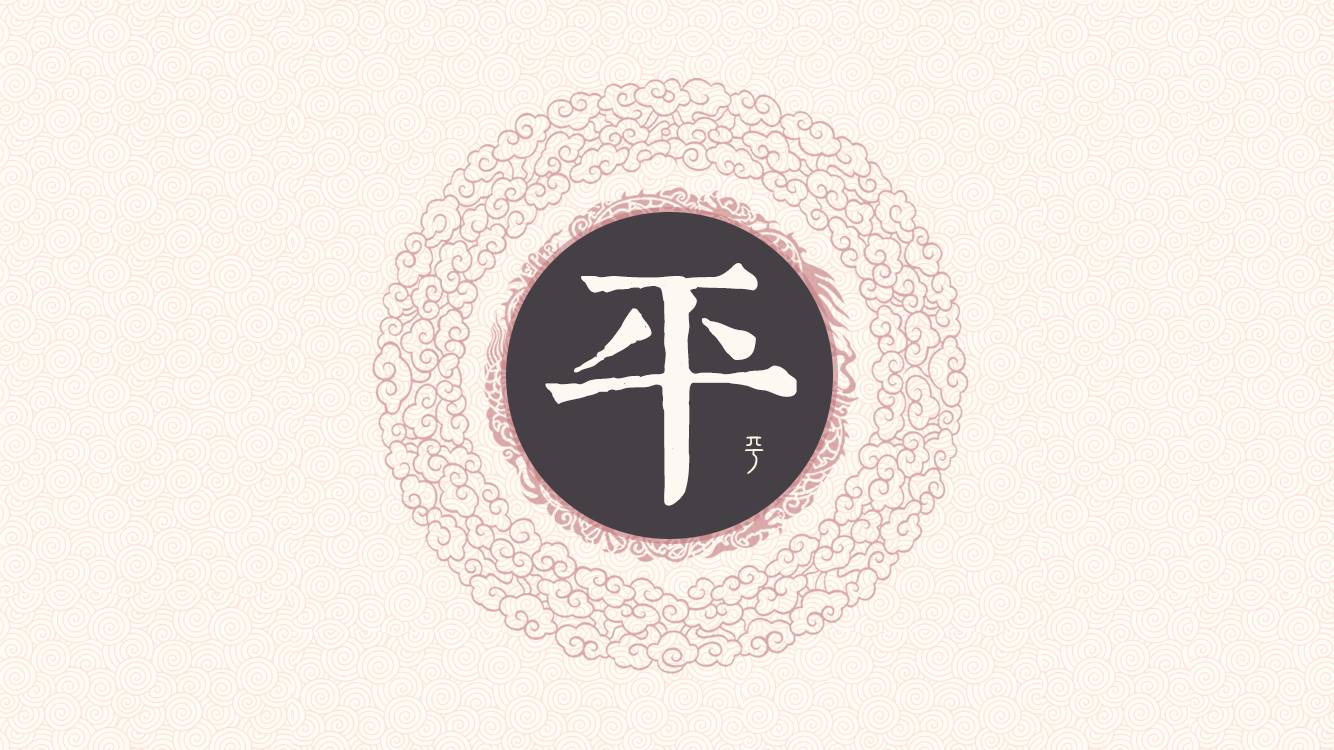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