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莼客传
平步青 撰
君姓李氏,初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气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生有异才,年十二三即工韵语,集中所存《游兰亭》诸诗是也。长益覃思劬学,于书无所不窥。时越多高才生,咸推君为职志。道光庚戌,吴县吴晴舫侍郎再督浙学,侍郎汉学大师,得君文,伟爱之,以第二人补县学生员。次年食饩,而应南北试凡十一,屡荐屡报罢。咸丰己未,北游,将入资为部郎,而为人所绐,丧其资,落魄京师。母恭人亟鬻田成之,李氏越中巨族,以财力滋殖雄里闾,君授产故不丰,至是儽然寒士矣。同治乙丑,请急归奉母讳。庚午,始举浙闱,五上春官,光绪庚辰始通籍。君才望倾朝右,佥谓宜擢上第,而顾不遇,以原官久次补户部江南司资郎。大都尚气声,交游造谒报谢无虚日,暇则征歌狎饮以为常,鲜治事者,而君独键户读书,吟咏莳药种花,非其人不与通,经年不一诣署。尚书朝邑阎公方严核名实,下教诸曹郎,分日入谒,尚书坐堂皇,旁一司官执簿唱名,堂下声诺如点隶呼囚者然。吏持牒至,君手书累千言,责其非政体,不当辱朝官而轻量天下士,伉直激切,若昌黎《与张仆射书》,走笔付吏去。阎公得书,颇善之,事遂已。己丑试御史,庚寅补山西道监察御史,转掌山西道,巡视北城,督理街道,皆举其职。数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权要,被旨允行或报闻,君顼顼不自得。今年夏,倭夷犯边,败问日至,知君者颇讶何以无所论劾。盖君戌削善病,至是独居深念,感愤扼腕,咯血益剧,遂以十一月十四日竟卒,年六十有六。
君自谓于经史子集以及稗官梵夹、诗余传奇,无不涉猎而抟抚之,而所致力者莫如史。所为散文、骈体、考据、笔记、诗歌、词曲,积稿数尺,而所得意者莫如诗,读者以为定论。君性简略,胸无城府,然矜尚名节,意所不可,辄面折人过,议论臧否不轻假借。苟同,虽忤枢辅不之顾,以是人多媢之。然虚中乐善,后进一言之合,誉之不容口,所指授成名者为多,门下著录甚众,诸生故人有改而北面者,它可知已。
君于经学,有《十三经古今文义汇正》《说文举要》《音字古今要略》《越缦经说》;于史,有《后汉书集解》《北史补传》《历史论赞补正》《历代史剩》《闰史》《唐代官制杂钞》《宋代官制杂钞》《元代重儒考》《明谥法考》《南渡事略》《国朝经儒经籍考》《军兴以来忠节小传》《绍兴府志》《会稽新志》;又有《越缦读书录》《越缦笔记》《柯山漫录》《孟学斋古文内外篇》《湖塘林馆骈体文钞》《白华绛跗阁诗初集》《杏花香雪斋诗二集》《霞川花隐词》《桃花圣解庵乐府》,凡百数十卷,可谓硕学鸿文,蔚为著述者矣。友人仅刻其《骈体文钞》二卷、《诗初集》十卷,余未厘定,传之其人。娶马恭人,无子,以弟之子孝琜为嗣。
论曰:吾越奇才,近代推石笥胡征君。御史后出,所学与征君微不同,其论定国朝古文,以征君为六家之一。征君性刚任气,豪荡自喜,不俯循咫步,为朝贵所恨,卒以穷死。御史晚达,入台谏,遇矣,而亦不克大显所蓄,卒憔悴诧傺以殁,不可谓非穷也。然征君有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 呜呼!谁谓御史而竟死哉!
白话文:
李先生,最初名叫李模,字式侯,后来改名叫李慈铭,字气伯,号莼客,是浙江会稽县人。他生来就有非凡的才华,十二三岁时就擅长写格律规整的诗文,他文集中收录的《游兰亭》等诗作就是证明。长大后,他更加深入思考、勤奋治学,对各类书籍无不广泛研读。当时浙江一带多有才华出众的读书人,大家都推崇他为求学的榜样。
道光庚戌年(1850 年),吴县人吴晴舫侍郎第二次担任浙江学政,吴侍郎是汉学领域的大师,看到李先生的文章后,非常赏识喜爱,将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补授为县学的生员。第二年,李先生获得了官府供给的膳食(即成为 “廪生”),之后他参加南北各地的科举考试共十一次,多次被考官推荐却始终未能考中进士。
咸丰己未年(1859 年),李先生北上游历,打算捐纳钱财担任六部的郎官,却被人欺骗,耗尽了钱财,在京城失意落魄。他的母亲恭人急忙变卖田产才帮他解决了困境。李氏家族本是浙江中部的大族,凭借财力积累在乡里称雄,但李先生继承的家产原本就不多,到这时就彻底成了贫寒的读书人。
同治乙丑年(1865 年),李先生因母亲去世,请假回乡守丧。同治庚午年(1870 年),他才在浙江乡试中考中举人,之后五次参加会试(明清时称礼部为 “春官”,会试由礼部主持,故 “上春官” 即参加会试),直到光绪庚辰年(1880 年)才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仕途。
李先生的才华和声望在朝中大臣中广受推崇,众人都认为他应当被提拔到更高的职位,但他却始终未能如愿,只能凭借原有官职的资历,按年资递补为户部江南司的资郎(清代对候补、候选郎官的一种称呼)。当时大多做官的人崇尚声势交际,日常往来拜访、答谢的事务不断,闲暇时就听歌饮酒,习以为常,很少有人专心处理公务。但李先生却独自闭门读书,平日里吟诗、栽种草药花卉,不是志同道合的人就不与交往,甚至一整年都不到官署去一次。
担任户部尚书的朝邑人阎公(指阎敬铭)处事严明,注重考核官员的名声与实绩,他下令各部的郎官按日子轮流进署拜见,自己坐在厅堂上,旁边有一位司官拿着名册点名,堂下官员应答的声音,就像差役呼喊囚犯一样。有官吏拿着公文来到李先生面前(要求他遵守这一规定),李先生亲手写下上千字的文书,指责这种做法不符合朝廷体制,认为不应当侮辱朝中官员、轻视天下的读书人,言辞刚直激切,就像韩愈(昌黎先生)写《与张仆射书》(反对张仆射让官员参加马球活动以辱官员)一样,挥笔写完后就交给官吏送去。阎公看到文书后,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这件事也就就此作罢。
光绪己丑年(1889 年),李先生通过御史选拔考试,庚寅年(1890 年)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后来转任掌管山西道监察御史事务,同时负责巡视京城北城、管理街道事务,他在各个职位上都尽职尽责。他多次向朝廷呈递密封的奏章,精准指出时政的利弊,从不回避权贵显要,他的建议有的得到皇帝圣旨批准施行,有的虽被朝廷知晓却未采纳,对此李先生常常显得失意不乐。
今年夏天,日本倭寇侵犯边境,战败的消息每天都传来,了解李先生的人都很惊讶他为何没有上疏议论弹劾(相关官员)。原来李先生向来体弱多病,到这时他独自在家深思国事,心中愤慨不已,以致咯血症状更加严重,最终在十一月十四日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李先生自称对经史子集以及野史、佛经、词、传奇等各类书籍,无不广泛涉猎并深入钻研,而他最为专注用力的领域莫过于史学。他所创作的散文、骈体文、考据著作、笔记、诗歌、词曲,积累的文稿有几尺厚,其中他最满意的作品是诗歌,读者也认为这是公认的定论。李先生性格简率,胸无城府,但十分看重名节,遇到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就当面指出别人的过错,评论人物好坏时从不过于迁就。如果是他认同的道理,即使会触怒朝中宰辅大臣,他也毫不在意,因此很多人嫉妒他。但他待人虚心,乐于行善,后辈读书人只要有一句话说得合他心意,他就会不停地称赞,经他指点而取得成就的人有很多,门下收录的弟子也为数不少,甚至有原本是他的学生或老朋友,后来改为拜他为师的,其他方面(他的受人推崇)就可想而知了。
李先生在经学方面的著作,有《十三经古今文义汇正》《说文举要》《音字古今要略》《越缦经说》;在史学方面的著作,有《后汉书集解》《北史补传》《历史论赞补正》《历代史剩》《闰史》《唐代官制杂钞》《宋代官制杂钞》《元代重儒考》《明谥法考》《南渡事略》《国朝经儒经籍考》《军兴以来忠节小传》《绍兴府志》《会稽新志》;此外还有《越缦读书录》《越缦笔记》《柯山漫录》《孟学斋古文内外篇》《湖塘林馆骈体文钞》《白华绛跗阁诗初集》《杏花香雪斋诗二集》《霞川花隐词》《桃花圣解庵乐府》,总共一百几十卷,真可以说是学问渊博、文章宏大,在著述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友人只刻印了他的《骈体文钞》二卷、《诗初集》十卷,其余著作还没来得及整理定稿,(有待)传给合适的人(继续整理出版)。李先生的妻子是马恭人,他没有亲生儿子,就把弟弟的儿子李孝琜过继为子嗣。
评论说:我们浙江的奇才,近代首推石笥先生胡征君(指胡天游)。李御史(指李慈铭)是后来出现的人才,他的学问与胡征君略有不同,但他在论述清代古文时,仍将胡征君列为清代古文六大家之一。胡征君性格刚直,意气用事,豪放不羁,不懂得顺应时势、谨慎行事,被朝中权贵怨恨,最终因穷困而死。李御史晚年才踏入仕途,担任监察御史,(相比胡征君)算是得到了机遇,但也没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学抱负,最终在失意困顿中去世,不能说他的一生不困厄。然而胡征君曾说:“从古至今的人都会死亡,只有能写出好文章的人不会真正死去。” 唉!谁说李御史就这样去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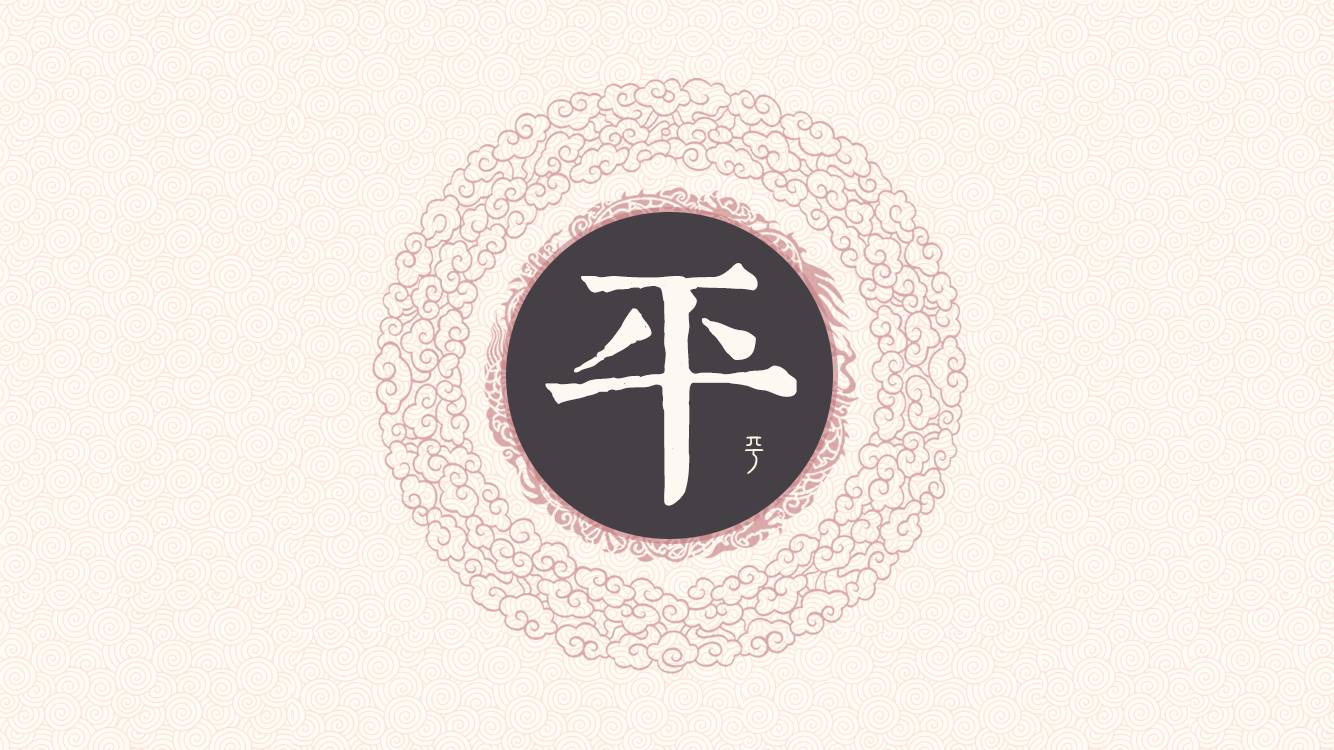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