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婆婆平自秀:清明寄思,往事如昨
婆婆平自秀生于1932 年 2 月 21 日,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与世长辞,享年 91 岁。您走后,日子依旧流转,可思念却总在不经意间翻涌 ——想给您献束花,也想和您说说心里话,就像从前那样,只有我们两个。
您的一生:从风雨里走来,把温暖都给了家
1932 年,您出生在一个还算富裕的小地主家庭,家里有薄田租给佃农,父亲还短暂当过国民党保长,日子过得殷实。您是家中长女,母亲后来又添了 2 个妹妹、1 个弟弟,一家人和和乐乐,本是人人羡慕的光景。
可命运偏要在您的人生里撒下荆棘。6 岁那年,母亲突然离世,父亲续弦后,后妈待您虽不及亲妈贴心,日子也算能过。只是后妈又生了 3 个孩子,家里人口多了,经济渐渐拮据,您初中只读了半年,就不得不辍学,从此再没踏进过校门。16 岁(1948 年)时,父亲也走了,未成年的您成了孤儿。后妈无力抚养 6 个孩子,只好带着你们改嫁,再后来又添了 3 个弟妹,9 个孩子挤在一个家里,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土改浪潮中,家里的土地被没收充公,本就困顿的家彻底没了依靠。没人照料的您,常常吃不饱饭,浑身脏兮兮的,身高也停了生长,曾经的 “大家闺秀”,竟落到近乎乞丐的地步。好在后妈心善,看着您这样实在心疼,便在 1952 年(您 20 岁时),给您说了门亲事 —— 嫁给了在云门镇做酱油的爷爷,那个出身贫苦却有手艺的穷小子。
爷爷幼年当小工,后来学了做酱油的手艺,解放前还和人合伙开了酱油铺,日子勉强过得去。解放后酱油铺并入供销社,爷爷成了工人,您婚后也进了供销社,总算有了安稳的着落。爷爷没读过书,是个文盲,他的大哥、二哥早年被抓壮丁编入川军抗日,从此杳无音讯,大概率是埋骨他乡了。或许是见三哥家有 9 个孩子,爷爷也觉得 “多子多福”,婚后便让您接连生孩子 —— 从 20 岁到 30 岁,您最美好的十年,都在 “怀孕、生子、养孩子” 和供销社工作的循环里打转,前后生了 10 个孩子,可惜最小的两个没能留住,最终拉扯大 8 个孩子。等最小的孩子成年时,您已经 48 岁,28 年的时光,都耗在了养育子女的辛劳里。
本以为能歇口气,可家庭的责任又找上了您。1981 年(您 49 岁时),我出生了。爸妈工作忙,把我寄养在乡下亲戚家,才两三个月,您和妈妈去看我,见我浑身脏兮兮地躺在地上的襁褓里,瞬间就心软了。您毅然辞了供销社的工作,又扛起了带我的担子。我在云门镇和您、爷爷一起生活了 3-4 年,那些模糊的记忆至今清晰:长长的昏暗过道通向家,小小的窗户透进微光,布帘隔开的 “厕所” 里摆着尿桶,院子里的水井,还有水井后大片的农田 —— 那是我童年最暖的底色。等我 4 岁回到爸妈身边时,53 岁的您,已经添了许多白发,显了老态。
可您的辛劳还没停。老三的女儿出生,您不顾成都和云门相隔遥远,去帮忙带娃,却因育儿观念和三嫂起了矛盾,带着委屈离开;后来老四、老五、老六的孩子出生,您快 60 岁了,身体早已吃不消,却还是尽力关爱每个孙辈;65 岁时,老七的孩子出生,您又一次动身去帮忙,可矛盾还是没能避免,最终不欢而散。您一次次怀着真心帮衬家人,却常常得不到理解,可这些委屈从未改变您的淳朴 —— 您对家人的关照,从来都是毫无保留。
我的思念: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小碎片
婆婆,这里没有其他人,就我们两个说说话。以前我在国外,回来的时间太少太少,现在想陪您,却再也没了机会。
2001 年我离开重庆去新西兰留学,走之前特意来看您。您一直念叨 “新西兰好远啊,为什么要走这么远”,您哪里懂,后辈总想着去更远的地方看看,可那时的我,竟没多陪您说说话。您一直送我到车上,还特意买了橘子,那场景,像极了朱自清笔下《背影》里的站台。车开走的时候,我听见您在后面一直喊我的名字,那声音,到现在还能清晰地想起。
小时候,您常去合川公园和其他老人跳舞,我就趴在广场旁边的栏杆上看。翻来覆去总是那几首舞曲,还有几首英文歌,我听不懂歌词,却把旋律记了这么多年。最近不知道在这边哪个超市,突然听到了熟悉的调子,瞬间就想起您在公园里跳舞的身影 —— 您穿着朴素的衣服,跟着节奏慢慢晃,脸上带着浅浅的笑,那样的画面,怎么也忘不掉。
这些日子,经常会梦见您,梦见您在院子里择菜,梦见您喊我吃饭,梦见您还是我记忆里的模样。我一直都很想您,您在那边,一定要好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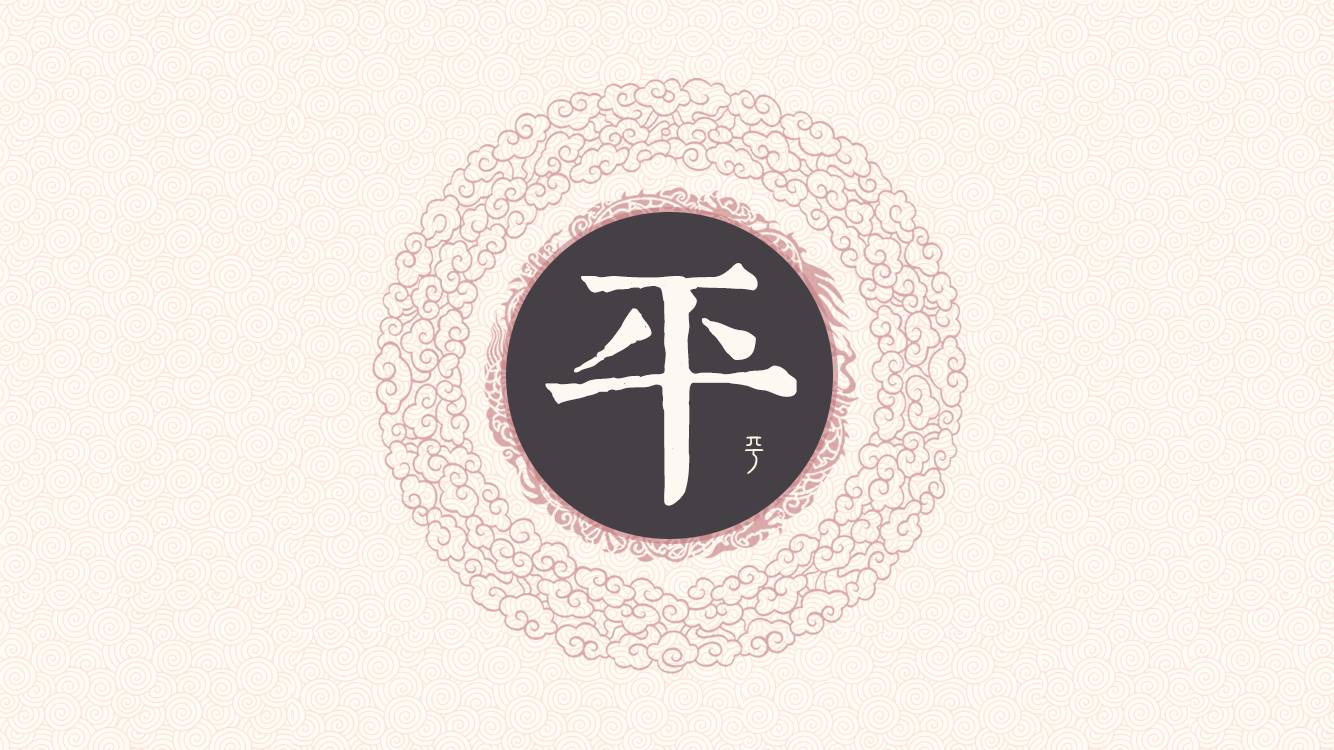

婆婆平自秀故于2023年6月15日,享年91岁。
婆婆于1932年在当时比较富裕的小地主家庭出生。爸爸短时间当过国民党保长。
家里有点薄田,一家人靠租地给佃农种过日子。婆婆是家里的老大,她的妈妈后续生了2个女孩和1个儿子。日子过得很殷实。
不幸的是在婆婆6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爸爸娶了后妈。后妈对待她肯定不如亲妈,但日子也能过下去。后妈和她爸爸又生了3个孩子。于是家里的人口就更多了。
因为经济开始拮据,婆婆初中只读了半年,就被要求辍学了。从此婆婆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到了婆婆16岁(1948年),爸爸又去世了。未成年的婆婆成了孤儿。她的后妈一个人无力抚养6个孩子,于是带着孩子改嫁他人。后妈和他老公又生了3个孩子,家里就有了9个小孩。
两年后,新中国成立了。小地主的婆婆家成了土改对象,土地被没收充公。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更加无以为继。
婆婆这个孤儿无人照料,一身脏兮兮的,经常吃不上饭,身高也没有再长了,曾经的大家闺秀几乎变成乞丐。
后妈终究是个善良人,思忖着这样下去不行。于是给婆婆张罗着嫁人。在婆婆20岁(1952年)时给她说了门亲事,嫁给了一个在云门镇做酱油的穷小子,就是我的爷爷。
爷爷是个技术工人,小时候给人家当小工,后来拜师学了门做酱油的手艺。解放前在镇上和人合伙开了个酱油铺。日子过得还可以。
解放后私营企业要被公家兼并。于是酱油铺变成了供销社的一个小作坊。爷爷从小老板变成了供销社工人,仍然做酱油。
他们婚后,婆婆也成了供销社的工人。她总算是有了着落。
爷爷没有读过书,是个文盲。他有三个哥哥,他排第四。老大老二被国民党抓壮丁去打日本鬼子,加入了川军。后来了无音讯。可能是死在了战场了。那时候兵荒马乱,两个大头兵的生死无人问津。
三哥结婚后生了9个孩子。爷爷可能也觉得生多了很好。于是结婚后每年都让婆婆怀孕生子。连续生了10个孩子。
但是最小的两个夭折了。于是婆婆最后有了8个孩子。
从她20岁到30岁这最美好的十年,她全部时间都在生孩子,养孩子,同时还要工作。非常辛苦。
等最小的孩子成年,婆婆已经是48岁了。
抚养孩子很艰苦,承担了家庭重担28年的婆婆已经不想再带小孩了。但是老大的小孩,也就是我,在她49岁的1981年出生了。
开始婆婆坚决不再带小孩了。我的妈妈和爸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把我寄养在乡下一个亲戚家代养。
只寄养了两三个月,当妈妈和婆婆去亲戚家看到我浑身脏兮兮地躺在放在地上的襁褓里的时候,婆婆心软了,她不得不辞去供销社的工作,又开始回到带孩子的生活中。
我在云门和婆婆爷爷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可能有3-4年吧。中间很多的记忆很模糊。
只记得长长的昏暗的通向婆婆家的过道。小小的窗户。一个小布帘隔开的摆着一个尿桶的“厕所”。院子里的水井和水井后面大片的农田。
等我4岁离开婆婆家回到爸爸妈妈家,婆婆已经53岁了。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这时老三的女儿出生了,老三家住成都,和云门相隔很远。婆婆仍然离开家乡去成都带小孙女。
但是因为带孩子和三儿媳妇产生了矛盾,婆婆愤愤地离开了老三的家。
儿媳妇们都说婆婆脾气不好,很急躁。但是后来还是能理解一个带了8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情绪不可能很平和。
等到老四老五老六的孩子相继出生,婆婆快60了。她实在有心无力带孩子了。
即使如此,婆婆对她所有的孙子孙女都尽力关爱。虽然没有带大他们,但是所有的孙辈都感受到了婆婆对他们的感情。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也了不起的事情。
在老七的孩子出生以后,她再次踏上离开家乡去帮助带娃的路途。这时她已经65岁。这次仍然和儿媳产生了矛盾,不欢而散。
每次带着关怀去帮助家人,却经常无法得到理解和尊重。这些仍然没有影响她淳朴的感情世界。她始终对家人关照备至
签名:冯田 2024/6/15 11:14
婆婆,今天是你的祭日,愿你在天堂安息,保佑我们子孙后代平安。想你
签名:冯田 2024/4/5 14:01
经常都会梦见您,清明节到了,给您献个花。
01年我离开重庆到新西兰留学,走之前来看您。您一直念叨新西兰好远,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后辈有时候就是这样,会走很远的。
您一直送我上车,还买了橘子。有点像朱自清的站台里的那样。车开走了,我听到您一直在后面喊我的名字。
签名:冯田 2023/11/21 18:11
这里没有其他人,就我们两个说说话。以前我在国外,回来时间太少,太少时间陪你。
在我小时候你经常去合川公园和其他老人跳舞,我趴在广场旁边的栏杆上看着你们跳。
翻来覆去播放的舞曲都是那么几只,其中有几首英文歌曲,我听不懂意思,但是旋律我不会忘记。
最近不知道从这边哪个超市听到了这个曲子,就想起你在公园跳舞的身影。
签名:冯田 2023/11/21 18:02
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