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留春書屋詩集十有二卷,臯辛酉座主平餘山先生之所作也。先生爲人醇粹和易,接物以誠。與人言訥然如不出諸口,操筆爲詩文則藻思逸情,傾瀉滿紙,汨汨不能自休。而不矜奇,不騁博,範才以就矩,審器以協音,醇粹和易一如其爲人。
至於吟賞節序,摹繪景物,更有工妙獨到、超然色想之外者。昔人論詩,謂管秘竅於寸心,争精微於一字,先生有焉。
先生家浙水,少游江西,歷海南,旣官京師,復奉命視學羊城,徧厯諸粤。嗣又乘軺攀桂,林眺鍾阜,兩任江蘇學使,搜奇訪古,悉寓之於詩。蓋風雅之宗,亦江山所助也。
年未六十,遽攖疾易簣于曁陽使院,胠行篋遺稿盡佚。賴同年友李松雲、許秋岩諸先生蒐討而存之,門下士復博采而增訂焉。其後王藝齋觀察重加釐輯,以遺朱虹舫閣學,遂偕同人謀付剖劂,而留春書屋詩始裒然成集矣。
鋟旣竣,虹舫囑臯爲序。臯不知詩,于斯集未能窺見什一,何敢云序?顧念先生性耽詩,生平所作甚富,今僅存此。且旣殁垂三十年,始克成是編,則其端緒不可没也。藝齋觀察旣叙其詮次之由,不揣檮昧,更綴數行以著之。若以云序,則何敢。
道光九年春三月旣望,受業金匱顧臯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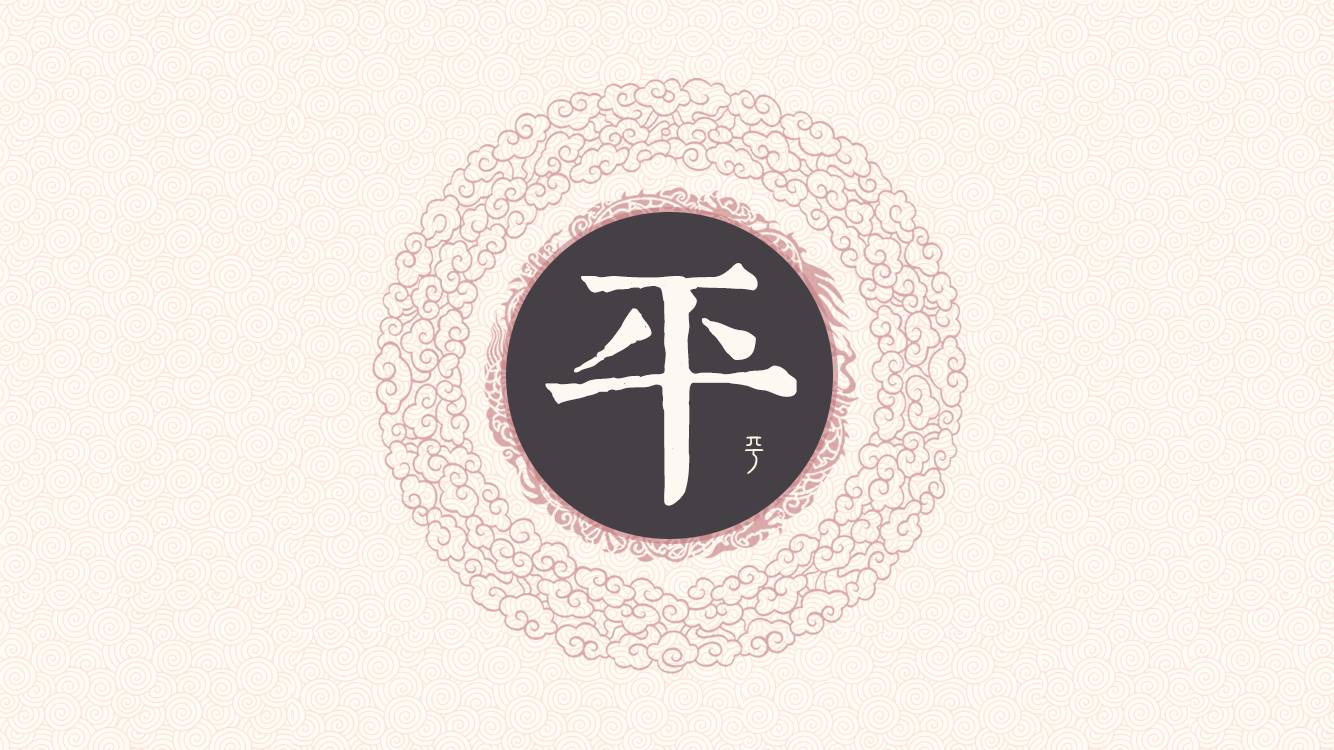

《留春书屋诗集》共有十二卷,是我(顾皋)辛酉年科举时的座师平余山先生(平恕)的作品。
先生为人纯粹温和、平易近人,待人接物秉持真诚。和人交谈时,他显得不善言辞,仿佛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可拿起笔创作诗文时,却文思敏捷、才情洒脱,文字如泉水般倾泻满纸,滔滔不绝难以停歇。他的作品不刻意追求新奇,不炫耀渊博学识,而是以规矩约束才思,使文辞与音韵协调相合,文风的纯粹温和,和他的为人一模一样。
至于那些吟咏节令、描摹景物的诗作,更有精妙独到之处,意境超然于外在表象之外。古人谈论诗歌,说要在内心深处把握创作诀窍,在一字一句间斟酌精微,先生的诗作正是如此。
先生祖籍浙江,年轻时游历江西,还到过海南。在京城做官后,他又奉命前往广州担任学政,走遍了广东各地;随后又奉命赴桂林、南京等地,两次担任江苏学政。他寻访奇景、凭吊古迹的所见所感,全都寄托在诗歌里。这既是因为他本身是风雅之事的宗师,也得益于江山胜景的滋养启发。
先生还没到六十岁,就突然患病,在江阴的学使官署中与世长辞。他随行箱子里的遗稿几乎全部散失,幸好依靠同年友人李松云、许秋岩等先生搜集寻访才得以留存,门下弟子又广泛采集补充修订。后来,王艺斋观察对遗稿重新整理编辑,将其赠予朱虹舫阁学,朱阁学便与同人商议刻印出版,《留春书屋诗集》这才完整成书。
诗集刻印完毕后,虹舫先生嘱托我为诗集作序。我并不通晓诗歌,对这部诗集的理解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怎敢谈作序?但想到先生生性酷爱诗歌,一生创作极为丰富,如今留存下来的只有这些;而且先生去世后将近三十年,诗集才得以编成,这份成书的缘由和过程实在不该埋没。王艺斋观察已经记述了诗集编辑整理的经过,我不揣冒昧,再补充几行文字来记录此事。如果说这是 “序”,那我实在不敢当。
道光九年(1829 年)春季三月十六日,受业弟子金匮顾皋恭敬书写。